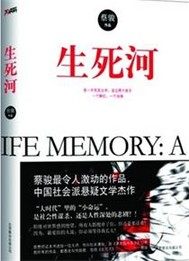漫畫–AQUARION COMPLETE–AQUARION COMPLETE
1995年6月19日,乙亥年壬午月辛巳日,舊曆五月二十二,戌時,兇,“日時相沖,諸事不宜”。
我死於子時。
每年晴與春分,我都會去給阿媽上墳,每次通都大邑加劇對身故的領悟。而死後還有人記憶你,那就不算真殞,起碼你還活在該署身體上。即躺在一座無主孤墳中,至少你還活在後人的DNA裡。不畏你連些微血脈都沒留給,丙還有你的名字與像,留在優惠證、使用證、戶口簿、借書卡、游水卡、電話簿、結業考卷……我多怕被大方丟三忘四啊!我叫表,曾是唐代中學高三(2)班的事務部長任。
我剛殛了一下人,而後又被其它人幹掉。
在扔田舍僞的魔女區,有把刀刺入我的後背。
戴着綴有紅布的黑紗,我自負親善始終睜考察睛,傳說中的心甘情願,但我沒察看剌我的兇手的臉。
是否停止呼吸?招有並未脈搏?頸翅脈還搏動嗎?血水不再注了嗎?氧氣黔驢之技消費大腦?終極發生腦玩兒完?毫釐無精打采得親善是。
發覺弱敦睦的消失,便是死嗎?
人人都說死的天道會很困苦,不論是被砍死吊死掐死悶死毒死滅頂撞死摔死甚至病死……接下來是限的孤身一人。
大學時日,我從學塾展覽館看過一本科普書,對此碎骨粉身過程的形容令人紀念深刻——
刷白筆直:一樣來於殞滅後15到120毫秒。
屍斑:遺骸較低部位的血下陷。
屍冷:殞命下超低溫的大跌。體溫平凡會安居大跌,直到與環境溫度一碼事。
屍僵:屍體的四肢變得梆硬,礙口轉移或舞獅。
仙劍跨世代
退步:遺體理會爲精煉式質的過程,伴隨着旗幟鮮明嗅的氣息。
耳性不易吧。
遽然,有道光穿透暗沙田底。我來看一條與衆不同的車道,邊緣是璋的塗料,像魔女區的優良,又像古老的克里姆林宮。特技下有個小雄性,穿衣打布條的稀衣衫,流考察淚與涕,趴在身故的母身上淚如泉涌,幹的男人漠視地抽着煙——應聲作嘹亮的噓聲,他也變成了一具屍體,後腦的洞眼冒着烽火,鮮血逐漸流了一地,沒過小男孩的腳底板。有中年娘兒們牽着男孩,走進一條安寧的街道,標語牌上黑糊糊寫着“困路”。這是棟古的屋子,雌性住在窖的窗牖末尾,每場冰雨天擡頭看着飲水奔流的大街,人人金燦燦或髒亂差的套鞋,有時候再有老小裙襬裡的隱私。雌性雙眼鬱悶,從未一顰一笑,臉煞白得像幽魂,就兩頰煞白,氣氛時愈發駭然。有天漏夜,他站在地下室的窗邊,街劈頭的大拙荊,鳴悽風楚雨的慘叫聲,有個異性步出來,坐到門口的階上嗚咽……
我也想哭。
但我單一具屍體,不會與哭泣,只會流膿。
短平快我將成火山灰,躺在坑木或硼鋼的小煙花彈中,酣睡於三尺以下的霄壤奧。恐怕,橫在魔女區道路以目冷的桌上,可觀腐成一團純潔的質,連老鼠與臭蟲都無心來吃,終於被植物吞噬無污染,直到化一具年輕的架子。
而有陰靈……我想我盛離開身軀,親眼見見氣絕身亡的自我,也能觀看殘殺我的殺手,還能有機會爲友好忘恩——化作魔,兇的怨念,時久天長烙印在魔女區,甚或元朝高級中學周遭數千米內。
死後的領域,崖略是磨滅年華瞻的,我想這怨念會是世代的吧。
而人生活,就不可能永世,只有死了。
人從一出生胚胎,不就是以便期待殂嗎?只不過,我等待得太急促了一絲。
可能,你們中會有一度智囊,在奔頭兒的某拂曉或寒夜,查出羅織我的企圖實,再者抓住摧殘我的殺手。
誰殺了我?
若是還有來生?一經還有來生?假使還能重複來一遍?假定還能制止悉數準確和冤孽?好吧,教會主任凜然,固我剛殺了你,但一旦在其他小圈子欣逢你,我還是想跟你說一聲“對不起”!
類似睡了代遠年湮的一覺,肉身借屍還魂了感覺,徒整人變得很輕,差一點一陣產能吹走,心腸莫名賞心悅目——這是死去活來的突發性?
撐不住地站起來,迴歸魔女區,前頭的路卻那眼生,復流失排泄物的田舍,倒更像古籍合影裡的畫面。不甚了了失措地走了很久,即是一條黑糊糊的羊腸小道,彼此是淒厲的山林,泥土裡隱晦浮骸骨,還有夏夜裡的粼粼鬼火。顛響着貓頭鷹的嚎啕,常川有長着顏面的鳥兒飛越,就連肉身都是婆娘的狀貌,能否風傳中的姑獲鳥?
有條河攔阻我的後路,湖面竟然恐懼的血色,空虛海氣的冷風從坡岸襲來,捲起的濤瀾白濛濛藏着人影與發,怕是剛滅頂過一些船人。沿長河走了幾步,秋毫沒覺恐怖,才發生一座迂腐的引橋。粉代萬年青的鐵欄杆杆下頭,坐着個斑白的嫗,駝背着形骸不知多少歲了,讓我回溯兩天前才氣絕身亡的姥姥。她端着一個破茶碗,盛滿熱火朝天的湯水。她昂首看着我的臉,污不堪的眼神裡,袒露那種更加的怪,又稍痛惜地搖搖頭,鬧不幸乾涸的聲音:“庸是你?”
老婦把碗塞到我面前,我恨惡地看着那層湯桌上的油汪汪:“這是哎住址?”
“喝了這碗湯,過了這座橋,你就能倦鳥投林了。”
我的回合永不終結 動漫
故而,我信而有徵地拿起碗,抑制自個兒喝了下去。意味還不壞,就像外祖母給我煮過的臭豆腐羹。
老太婆讓到一面,促使道:“快點過橋吧,不然不及了。”
“不及投胎嗎?”
某个店员与客人的故事 go篇
這是我在宋史普高深造時的口頭禪。
“是啊,少兒。”
話說之間,我已縱穿這座新穎的望橋,伏看着身下的河水,滿貫家庭婦女短髮般繞組的鹼草。剛踏上坡岸漠不關心如鐵的糧田,就升起陣無語的反胃,不由得地跪下唚開班。
真心疼,我把那碗湯係數吐出來了。
當我還瓦解冰消轉回神來,私下的大江已平地一聲雷上漲,瞬間將我吞沒到了水底。
在長滿麥草竭白骨的黑燈瞎火坑底,夥同怪模怪樣冷言冷語的光從某處射來,燭照了一下人的臉。
弱小英雄演員
那是活人的臉,也是二十五歲的闡發的臉。
而我即將化作另一個人。
從前我不信託古書裡說的——人死後都要經幽冥,走上九泉之下路,在抵冥府之前,再有一條壁壘的忘川水。由河上的奈橋,渡過這條忘川水,就上佳去改扮轉世了。怎麼橋邊坐着一個老婦人,她的名字叫孟婆,倘不喝下她碗裡的湯,就過不興怎樣橋,更渡不已忘川水,但倘若喝下這碗孟婆湯,你就會忘記前生的滿記憶。
忘川,孟婆,來生。誠然會忘本整整嗎?
“而還有他日?你想怎樣扮演你的臉?假若毀滅前?要哪邊說再會?”